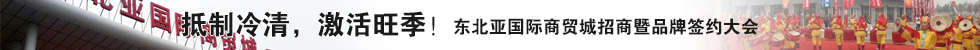17歲的盛夏,我的父母在法院外面打電話給我,最后一次征詢我的意見,問我到底要跟誰。我對他們既已失望透頂,跟誰又都不會是我最終的選擇,于是我說:“我就是我,不屬于你們任何一個。”后來,我就一直住在學校里,父母按時把錢匯到我的銀行賬號上,因為心有所欠,所以格外大方,高考后我去查那張銀行卡,已經積攢了很充足的一筆。
于是那年7月,我在城南租了一間小房子。房子有暗紅磚墻,白木窗框,樓下花圃里種滿了淡紫柔粉的薔薇,大樹上還掛著小孩遺落的秋千,有風時,它便晃來晃去。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我的父親遠去德國,而我母親嫁到了深圳,兩人都比我有出息。其實我也不錯,考上了本市的一所大學,讀一個無聊的信息管理與統計專業。
胡枷是開學第一天在校門口接新生的學長。他見到我,大眼睛一瞪,問我:“咦?你就這么來啦?行李呢?”我說我沒行李,辦好手續我還得回家睡午覺呢。后來,胡枷這家伙告發了我,害我逃宿的計劃破產,不得不住進學校的破宿舍樓。周末他來請罪,帶我去吃飯,他嘻皮笑臉地說:“為了你好,和大家住一起,才不會變態。”我們那天吃的是火鍋。一半紅湯滾沸,一半白水瑩瑩。我專挑紅色的辣味吃,表情猙獰,他就笑,笑了半天,也不說笑什么。于是我也跟著笑,面對一位善笑的男孩,人的心情是沒辦法不好的。
秋天的午后,我偶然爬上文科樓的天頂,遇見了正在畫畫的胡枷。他腳邊堆著成捆的畫稿,我抽出幾張,忽然看到了我自己。畫里,我表情猙獰,正在踞案大嚼。“知道嗎?這就是——豬的吃相。”他認真地說。
大概是從那天起,我開始試圖了解我自己。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喜歡的是什么?我的未來會怎樣?一支碳筆,一塊畫布,若干幻想,一個平凡的人就可以編織出不那么平凡的夢想。我拜胡枷為師,開始跟他習畫。幾乎每個周末我們都要到胭脂路去逛,和一群大媽大嬸一起在布堆里翻找,盡量用最便宜的價格淘到我們需要的白色厚布,這些布當然不是用來縫衣服的,而是做畫布。
我們就那樣畫了整整兩年。兩年里,我們畫掉了上百張畫布,兩大箱碳筆。深冬,學校的人都走了,就剩我們倆,像兩只細腳的鸛,立在文科樓的天頂,顯出傲岸蒼茫的樣子。雪就那樣落著,人像沉在海底,我冷得哆嗦,胡枷就說:“需不需要我溫暖的胸膛啊?”我走過去,很乖地鉆到他懷里。那一刻,我們貼得那樣近,幾乎疑心已成情侶。可是我知道,愛情這件事,有時候就像在寒天拾到發了潮的火柴,你怎么著急,它也擦不燃。
我們畫了那么多畫,積在天頂的破箱子里,快被蟲子吃光了。胡枷說:“我們辦個畫展吧,我們會成功的!”在市中心廢舊的小藝術館里,我們忙了三天三夜,精心地布置我們的畫展,累得快虛脫了。可是畫展開始那天,我卻沒有勇氣去看。胡枷去了,晚上他回來時我問:“看的人多嗎?”他罵了一句他媽的,說一整天還不到10個人。
那個晚上我們醉醺醺地摟在一起,坐在我們的天頂上,胡枷淡淡地勸我:“算了,不畫了。”仿佛在漫長的山洞里已走了大半程,四周寒冷黑暗,沒有火把,可是我的同伴忽然拋下我,獨自一人返程了,而我呢,我還在慢慢摸索,探尋著出路,饑寒交迫。
從此,胡枷果然不再畫畫,發奮參與學校的各種活動,很快成為學生里的官僚,后來,他當上學生會主席。而我又恢復到我孤單的生活里去,卻在春天的時候,忽然收到一封電郵。
來信者叫杜弋,住在離我很遠的城市里。他說,去年冬天,我出差路過你的城市,那天下雪,辦完事我獨自一人在街頭行走,看到了你的畫展。他說,當時看了,并沒有覺得特別好,可是很奇怪,我卻一直沒有忘記。他說,大概這就是歌里唱的“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吧。
是怎樣的一種觸感,像蜉蝣掠過水面,就那么微弱但真切地碰到我心里最柔軟的一角。畫畫是一件寂寞的事情,忽然知道遠處有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在關注著你,我覺得我真快樂。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他打電話給我,問我:“你一定很瘦對不對?”他又說:“要注意身體啊。”他說的話都很老生常談,有點像爸爸,不過,他比爸爸懂得我,他告訴我,在那部電影里,馬蒂達問里昂:“人生是從來都很寂寞,還是只有少年時如此?”里昂回答:“Always。”不是沒有人告訴過我,陌生男人多么危險,但是我無法將杜弋歸入這樣的戒備中去。
大三的夏天,胡枷畢業,儼然是一位青年才俊了。胡枷意氣風發,無往不利,戀愛了幾次,失戀了幾次,仍舊對結婚這件事充滿了向往。某個下午,他騎著單車從我的樓下經過,停住,然后揚起頭,沖我的宿舍大喊:“405的繹,你出來出來!”我走下樓去,看著他:“喝酒了?”“沒有。”“還嘴硬,要干嘛?我忙著呢。”“繹,我知道你不愛我,可是,我可不可以請你做我的女朋友?我知道你很寂寞,我也很寂寞,據說兩個寂寞的人在一起,就不會再寂寞。”我看著胡枷,胡枷有雙明亮的大眼睛,這樣一雙眼睛,光明磊落而又懂感恩。有這樣一雙眼睛的人是可以托付終身的人吧。我便說:“好。”
生命是冗長而沉悶的,愛情是短暫而珍稀的,用冗長的生命去等待短暫的愛情,似乎是不智的。就算等到了,電光火石的幾秒鐘,它已完成發生發展終止的全過程,而后歸于永恒的寂滅。而那時,我要用多少悵惘和無奈,去撫平愛情走后留下的傷痕累累呢。那么,不如就做一個踏實的人,和另一個踏實的人一起,安安心心地彼此溫暖,各取所需。
“你應該戀愛了,孩子。”那天晚間,收到杜弋的電郵,他也是這么寫。我為這心有靈犀而戰栗,又仿佛若有所失。杜弋再打來電話時,我開著免提,胡枷就在我身邊。我想讓胡枷知道,我和杜弋僅僅是朋友;也希望杜弋了解,我現在已經過著他所期望的生活了。
掛了電話,我與胡枷去吃晚飯,路過校園外嘈雜的菜市場,這大抵就是我們未來生活的寫照吧,這樣的瑣碎與俗常。我們都沒有說話,疲倦籠罩著我,而郁悶挾持著胡枷。那天晚上我回到我的寓所,忽然想給杜弋打電話,忽然就說:“你來看看我,來不來?”他真的來了。
似乎直到他來,我才發現原來我的城市也可以這樣燈火婉轉、波光滟瀲。夜晚,他下了飛機,站在機場外的燈光里,衣裳如云朵,他像一位圣者。這是五年來我們的第一次見面。
酒吧里有上好的黑椒牛排,恰到好處的梅子酒,吃過飯,我們在投幣點唱機里點一首古老的歌:“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把你的左手放在我的肩上,把右手放在我的手心里。”他說。我照做了。我們便在那酒吧的陽臺上跳舞,夜色深濃,天上有星子閃爍,幾乎是在瞬間,所有刻意和壓抑突然崩潰,我經歷的委屈,我受的傷害,在他面前,我終于肯哭出聲來。
他只停留了一天便走了,許多該說的話都語焉不詳地留在了半空中,像是塵灰吊子,我也無心打掃。我終于明白了我對他的感情,他是如此完美,恰好符合了我對愛情全部的期望,他完美到成了一種信仰,一種象征,所以,當這個完美的人忽然說“你本應該嫁給我的”時,我愣住了。
“記得嗎,有一個晚上,我發電郵給你,告訴你,你應該戀愛了。”“我收到了那封電郵。”“若你當時反問一句,與誰戀愛,我一定會回答,與我。”“你的暗示,太微弱了。”就這樣,他正式地成為我生命里的錯過,成為永遠的電光石火。
畢業后的秋天,我嫁給胡枷,成為他平凡的符合理想的妻。我不再畫畫,安心做著一個普通的小職員,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在中年以前,可以買到寬敞的住房、漂亮的車。三餐菜式四季衣裳,年復一年,我和胡枷過。
但我會憶起這位名叫杜弋的男子。他優雅,聰明,能夠聞弦歌而知雅意,可以自如地與我唱和,是我遇到的最可愛慕的人。但是我卻不能與他結為夫妻,因為,除開生命里早已安排好的陰差陽錯,我更舍不得他在以后的日子里變得庸俗、瑣碎、無聊,舍不得他的光芒消散在柴米油鹽之中。他只能活在回憶之內,現實以外,以一位圣者的形象,遠遠地和我站在一起。
于是那年秋來之后,我成為一個耽于安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