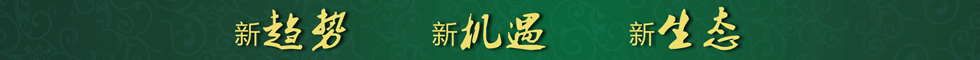住房改革又走在新的路上。用半市場、半保障的思路來解決“夾心層”群體住房問題,比“市場和保障相分離”的思路又前進了一步。
8月3日,北京出臺了針對“共有產權房屋”的征求意見稿,被全國關切。
此次北京提出的共有產權住房這一概念并非首創,在2014年4月份,住建部發布《關于做好2014年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已經確定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淮安、黃石為共有產權住房試點城市。
其中,淮安是全國范圍首個推出共有產權房試點的城市,早在2007年,江蘇淮安在全國首推共有產權住房。在此之后上海、黃石、成都等地從2009年至2014年相繼出臺各自版本的共有產權房新政。
走過10年共有產權住房政策施行時間的淮安,已經經歷3個階段,從最初的政府自建房到現在的貨幣化助購。每個不同階段,淮安市政府的共有產權政策重心都是針對不同發展階段地方所面對的各類問題而有所調整,從保障住房到去庫存。
這一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與上海、黃石和深圳等城市一樣,新政也遭受購房者熱情不足、權責不明晰以及有政府間接參與“炒房”的質疑。在這些質疑聲下,共有產權住房在不斷的修復中走向更加完善,也更適合各個城市所展現的不同實情。
擴大范圍
作為全國首個共有產權住房試點城市,淮安經驗從一開始來看并非立竿見影。檢驗這個政策是否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看共有產權住房推出后是否獲得市場的認可,事實上,在這樣一個自有商品房占比已經相當高的四線城市,最初的效果不盡如人意。
2007年10月,淮安市推出了首批300套共有產權住房。這300套住房面向的是自主購房者,而非拆遷安置戶。拆遷安置戶中的住房困難戶,同樣可以購買共有產權房。這些房源散落在新新花園、洪福小區和嘉潤苑三個小區,每平方米均價2300元。當時,市場價格約為每平方米2500元。
從當時的新聞報道來看,首批共有產權住房推出即“遇冷”。按照當時的設計門檻,人均收入低于400元/月的家庭,可以申購共有產權住房。隨之出現的一個情況是咨詢者眾多,但真正申請的卻很少。截至當年12月,實際申請家庭僅70戶。
淮安市隨后放低準入門檻,把人均收入放寬到700元/月,實際操作過程中,甚至放寬到800元/月。300套住房剛剛夠,也并未出現普通經濟適用房供不應求的局面。
雖然政策的出發點是希望通過改變原有的單純由政府提供廉價的經濟適用房的方式,實現政府減負與低收入群體有其屋雙重目標,不過事與愿違。從2007年到2015年的8年時間內,淮安市區共向1164戶家庭供應經適房共有產權房,其中僅有265戶家庭增購政府產權,共回籠資金不到1400萬元。
遇冷最關鍵的問題在于價格。2007年,淮安市創建與市場接軌的共有產權經濟適用房模式之初,房屋產權比例共有兩種模式:當個人與政府的產權比例為7∶3時,個人承擔的價格相當于同期經濟適用住房的價格;對仍無力購買的特殊困難家庭,可按5∶5的產權比例進行購買。
“這個7∶3的比例并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把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與普通商品房的價格比較后得出的一個比例。”制度設計者、當時的淮安市房管局局長邵明說。
即便如此,部分低收入群體依然難以支付70%部分達數十萬的房價。加之淮安市同時也在推行公租房政策,以每月低廉的價格租房成為更多人的選擇。如何將更多人納入共有產權房輻射范圍,于是將公租房納入共有產權住房的政策范疇成為當地政府的新目標。
在淮安市保障性住房建設管理中心彼時負責人劉遠勝看來,當時淮安公租房共有產權房擬定的思路是“先租后售”,即在承租滿兩年后,按出資不低于60%申請購買,形成共有產權住房。推行這一政策,也是出于實際需求。有的困難家庭在公租房里一住就是幾年,習慣了,就不想再動。轉租為賣的思路由此而生。
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淮安建成公租房3004套,1503套承租。如果將這一市場打開,地方政府將能回籠超過2億元,要知道2010年淮安市政府決定用3年時間興建7000套共有產權住房總耗資也就4億元。
雖然是依據實際需求出臺的政策,但市場對公租房共有產權政策反應平淡。截至2015年10月,淮安1503戶承租家庭中,還沒有一戶有買房的想法。“一單申請也沒收到!”劉遠勝彼時接受采訪時坦言。
直到2015年11月1日淮安市共有產權房申購家庭擴容,情況有所好轉。新政明確指出,將“進一步鼓勵符合條件的對象申請共有產權住房保障,對申請購買政府集中建設的共有產權住房的城市無房家庭的收入不作限制;對申請共有產權住房保障的新就業人員的婚姻狀況不作限制;對具有本市戶籍進入市區務工的人員申請共有產權住房保障其戶籍所在縣城住房狀況不作限制。”
既要有房住又要住得好
淮安,2010年前人口過500萬,雖然規模無法與一線城市相提并論,但當共有產權住房供應對象擴大時,資金壓力開始凸顯。“想讓共有產權住房模式轉起來,政府的資金是關鍵,但是隨著房價提高,政府保障金沒有那么多。”一位淮安地產人士告訴中國房地產報記者。
記者從淮安市政府網站上看到,共有產權住房政府承擔部分的資金來源是:拆遷項目屬經營性土地的,列入土地開發成本,在土地出讓成交后,及時足額提取共有產權房政府承擔資金。單宗地塊難以平衡的,在全年土地出讓中綜合平衡。拆遷項目屬非經營性土地的,原則上列入項目建設成本。
2010年,淮安市計劃3年投入4.1億元,2到3年內建成7000套共有產權住房,到2015年這個數字更高。如果考慮到不斷上漲的土地成本和房價,完成目標所花費資金將達到10億元以上。
除了資金問題之外,共有產權住房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也逐漸浮上水面,前述地產人士告訴記者,由于共有產權住房的購房者以中低收入人群為主,共有產權住房集聚的小區則會被人們扣上城市“窮人區”的帽子。
一方面要推進共有產權住房建設,與此同時還要避免共有產權住房建設過于集中,出現“窮人區”,淮安市在2014年開始采用“分散建設”共有產權住房來避免這一問題。
在當年3月淮安市推進共有產權住房綜合試點工作會議上,相關負責人提到對市共有產權住房政策進一步提升,全面對接普通商品住房市場,制定共有產權住房定向購買目錄,政府提供不高于40%的貨幣補貼,由保障對象在定向購買目錄內自由選購。
這個意見的主要操作方法是在開發商建設的樓盤中,由政府回購一部分,再以“共有產權模式”出售,讓共有產權房分散在普通居民小區中,這樣就可以解決共有產權住房過于集中的問題。
“從土地一級開發中脫離出來,政府在資金回轉的余地上有了更大的空間。低收入群體也被分散到正常的商品房小區之中,這也是這種實物+貨幣補助方式的意義”,前述地產人士告訴記者。
截至2017年4月,全市共有49戶符合條件的家庭由政府補貼、自己出資在商業樓盤購買了共有產權房。
不難看出,數量,依然是新政最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49套房子解決的保障問題與普通經濟適用房相比還不在同一個級別之上。“”當初推出共有產權房的時候,是一個全新事物,是一個試驗,因此沒有大規模推。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邵明說。
去庫存的新任務
作為全國首個試水共有產權住房的城市,淮安并不是十分理想的試水地。其商品房的去化周期是20個月左右,其中商品住房在16個月以內,共有產權住房進入市場將從一定程度上延長這一過程,但是2016年國內經濟工作“去庫存”主題給予淮安新的思路。
2016年3月6日,淮安市委書記姚曉東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去庫存的壓力不是很大,但是我們要未雨綢繆。”姚曉東表示,下一步要從幾個方面著手:其一,淮安是住建部確定的六個全國共有產權住房試點城市之一。買房人和政府可以各出一部分錢,共有房屋產權,解決低收入群體的買房需求。
共有產權住房被納入去庫存的思路,這就意味著原有政府自建模式要從供應源頭來一個轉向,“城市建設項目涉及征地拆遷,少建、不建安置房,多用貨幣化手段安置。給你錢,你去買存量房,不也消化了庫存嘛。”姚曉東說。
1年后,淮安的共有產權住房政策進入第三階段。2017年4月6日,淮安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處對外稱在淮安將不再新建共有產權住房,傳統意義上的實物共有產權住房已升級為貨幣化政府助購,即政府不再新建共有產權住房,而是由政府出資補貼,讓符合購買共有產權住房的購房者去購買商品房,政府與購房者的產權比例為4比6。
淮安10年共有產權住房經驗對北京有何借鑒意義尚不得知。8月3日,《北京市共有產權住房管理暫行辦法》正式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辦法明確,各區人民政府根據共有產權住房需求等情況合理安排共有產權住房用地。
經濟學家馬光遠認為,相對于淮安模式,北京市這次推出的“共有產權房”,房子的“商品屬性”更多,而保障屬性更少。但是,二者共同的問題仍然是“共有產權房”中政府所占份額以及定價問題。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擔心的是政府負擔問題。他認為北京等一線城市,人口輸入量大,房價過高,如果采用共有產權模式,政府墊資過高,需要考慮如何抵消套利。
另外,一線城市如采用此模式,因房價過高,政府墊資占比過低,無法解決中低收入家庭資金困難。如提高墊資占比,那巨額資金從何處來?這都需要實踐與摸索。